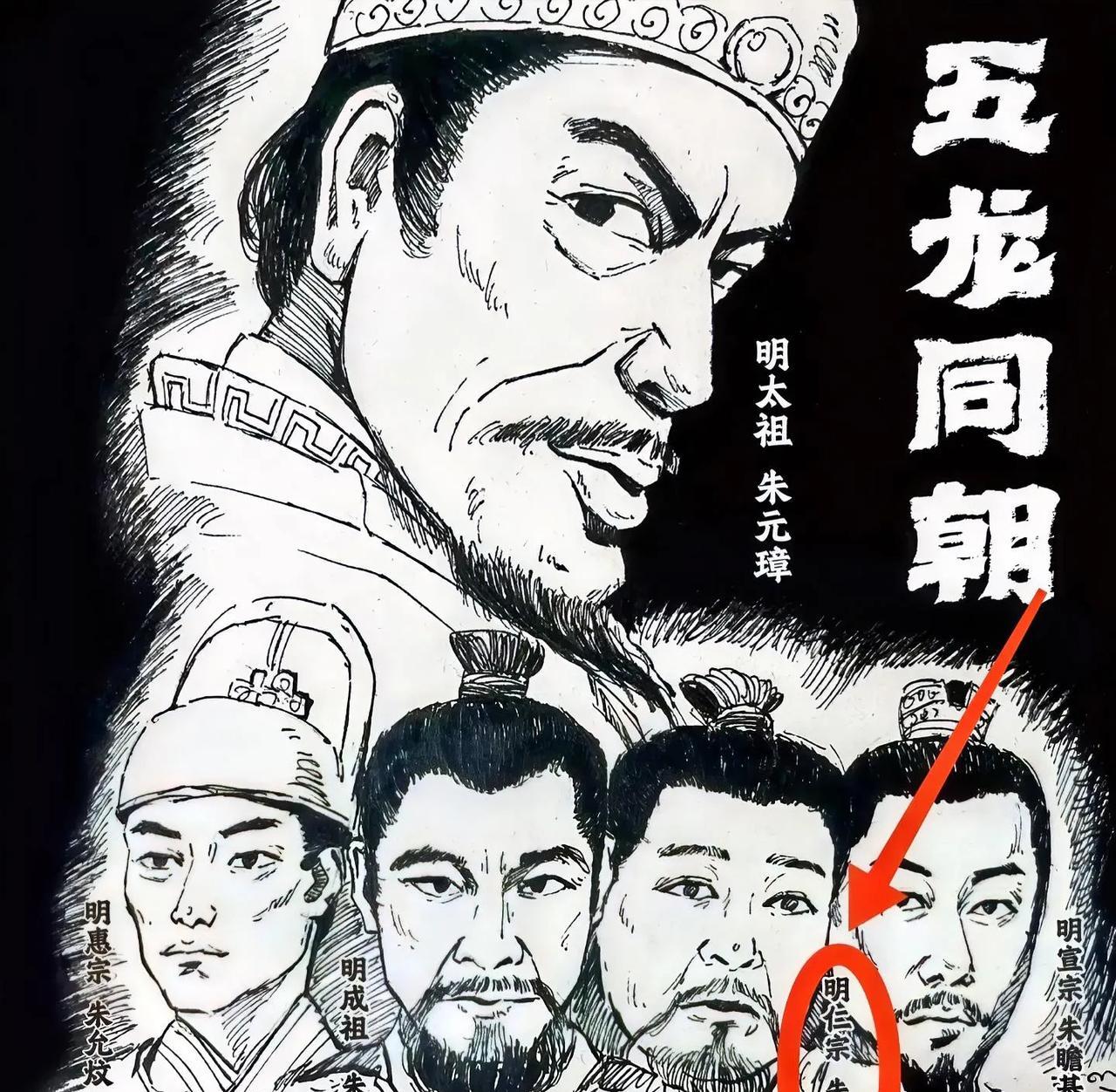1407年,朱棣的妻子刚过世,他就给28岁小姨子徐妙锦写信:嫁给我吧!徐妙锦回:
1407年,朱棣的妻子刚过世,他就给28岁小姨子徐妙锦写信:嫁给我吧!徐妙锦回:我染了天花!朱棣欣喜若狂:那更得娶你!徐妙锦被感动,害羞地送了朱棣1个信物,谁料,朱棣看后,脸色顿时阴沉,眼角闪过一丝杀机。永乐五年的冬月,仁孝徐皇后的梓宫停在坤宁宫,素幡白烛,冷得渗人。朱棣在灵前枯坐半日,直到暮色染透窗纸,才被内侍劝回寝殿。炭火烧得旺,却驱不散心头的空落。他挥退众人,独坐案前,目光扫过徐皇后生前常坐的锦墩,指尖无意识摩挲着腰间旧荷包——那是她早年亲手绣的,鸳鸯的翅膀已磨得发白。一个念头,野草般在空寂里疯长。他猛地起身,抓过紫毫,墨汁溅污了明黄笺纸:“妙锦吾妹:中宫新丧,朕心摧折。然六宫不可无主,朕亦需人扶持。汝乃皇后胞妹,温婉知礼,堪为继配。若得应允,即日入宫,朕当以中宫之礼相待。”信使马蹄踏碎宫道薄冰,将滚烫的诏书送入魏国公府。徐妙锦展开黄笺,指尖冰凉。她二十八岁,眉目间犹存少女清丽,却比深宫里的姐姐更早看透世情。皇帝姐夫?继后?她眼前晃过姐姐操劳至死的倦容,晃过宫墙内数不尽的孤灯长夜。那金碧辉煌的牢笼,她死也不愿踏进。“回禀陛下,”她提笔,墨迹凝滞,“臣女骤闻天恩,惶恐无地。然臣女身染恶疾,面生痘疮,形容可怖,实不敢以残躯污秽天颜,更恐贻害宫闱。万望陛下收回成命,另择贤淑。”信送回大内时,朱棣正对着一碗冷透的参汤出神。展开回信,“痘疮”二字刺入眼帘。他先是一怔,随即竟放声大笑,震得梁上灰尘簌簌落下。好个徐妙锦!竟拿天花搪塞他!这借口拙劣得可笑,却偏偏挠中了他心底隐秘的痒处!“染疾?”朱棣眼中燃起奇异的光,提笔如刀,“朕岂是俗人!莫说痘疮,便是阎罗亲索,朕亦要留你在侧!速备鸾驾,朕亲迎你入宫!”这近乎蛮横的诏书再抵魏国公府,徐家上下如坠冰窟。徐妙锦捏着信笺,指尖掐得发白。最后一丝婉转的余地也被堵死了。她独自走进闺房,铜镜映出一张苍白却决绝的脸。梳妆台上,一把银剪冷光幽然。几日后,一个紫檀螺钿盒送入乾清宫。朱棣刚下朝,龙袍未解,带着一身寒气。瞥见那盒子,心头一热。到底是女儿家,终究被他的“深情”打动?盒面精雕缠枝莲纹,触手温润。他嘴角噙笑,亲手揭开盒盖——没有预想的香囊玉佩。盒底红绒衬垫上,赫然是一绺乌黑发丝!剪得齐整,却断得决绝!发丝之上,静静躺着一枚小巧的三足铜香炉,炉腹微凹,炉口边缘残留着新焚的灰白香灰,一股浓烈到刺鼻的檀香气味混合着焦糊味,猛地冲了出来!朱棣脸上的笑意瞬间冻结。他死死盯着那绺断发,又猛地看向那枚香炉。炉是旧的,边缘磨损得光滑,显然是常用之物。香灰…是新的!她焚香?在断发之时焚香?!一个可怕的念头如同毒蛇,猛地噬咬住他的心脏!这断发,是斩断尘缘!这香炉,是供奉神佛!她徐妙锦…竟是要出家?“砰!”朱棣暴怒一掌,将紫檀盒狠狠扫落在地!盒盖碎裂,断发与香炉滚落金砖,香灰泼洒开来,污了明黄的袍角。“好个徐妙锦!”朱棣双目赤红,额角青筋暴突,声音从牙缝里挤出,带着骇人的嘶哑,“断发明志?焚香礼佛?朕的恩宠,在你眼里…竟成了逼你出家的劫难?!”一个臣女,竟敢如此羞辱天子!她徐家仗着是皇后母族,就敢如此放肆?!徐辉祖(徐妙锦之兄)当年在靖难时首鼠两端,这笔账还没算清!“传旨!”朱棣的声音如同九幽寒冰,每一个字都淬着毒,“魏国公徐辉祖,治家不严,纵容亲妹狂悖忤逆!着即…”“陛下!”一声凄惶的哭喊打断了他。徐皇后生前的贴身老嬷嬷不知何时跪在了殿外,白发凌乱,重重磕头,“陛下!万万不可啊!娘娘在天有灵啊!三小姐她…她是娘娘一手带大的,性子是倔了些,可万不敢对陛下不敬!求陛下看在娘娘的份上…饶了三小姐!饶了徐家吧!”“娘娘”二字,像一盆冰水,兜头浇下。朱棣猛地一窒,已到嘴边的“削爵”“下狱”硬生生卡在喉咙里。他眼前闪过徐皇后弥留时枯槁的面容…狂怒的火焰被强行压住,却烧得五脏六腑剧痛。他死死攥着拳,指甲深陷掌心,渗出血丝。许久,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:“滚……都给朕滚出去!”空荡的大殿里,只剩下朱棣和地上那绺断发、那枚倾倒的香炉。浓烈的檀香味顽固地弥漫着,像徐妙锦无声的嘲讽。他缓缓弯腰,捡起那绺青丝。发丝冰凉柔韧,缠绕在他指间。他仿佛能看见徐妙锦剪断它时,那双决绝的眼睛。再看向那香炉——她宁愿青灯古佛,也不愿踏入宫门一步!朱棣笑了起来,笑声阴冷,如同夜枭,“你想做尼姑?朕……成全你!”几日后,一道冰冷的旨意降下魏国公府:准徐妙锦出家,敕封“静慈仙师”,移居西城外一处皇家敕建的小庵堂“静慈庵”。无旨,终生不得出庵门一步。静慈庵落成那日,风雪漫天。徐妙锦一身灰色淄衣,步入庵门。庵门在她身后缓缓合拢,落锁声清脆。她回望一眼风雪中的北京城,目光平静无波。青丝已断,尘缘已了。这方寸静室,是她用决绝换来的囚笼,也是她远离滔天权势的净土。